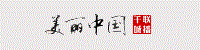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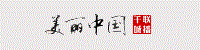
车在蔚蓝的天空下行驶,夏初的葳蕤袒露在阔野上,故乡大地一派生机。看呵,绿树含烟,鸥鸟翩翩;丰草争茂,流水潺潺;田畴如毯,麦浪绵绵。目力所及,皆是一幅线条明快、色彩斑斓的田园图画!
自从参军入伍,近三十年了,我离故乡与庄稼已渐行渐远。眼前这片一望无边的滚滚麦浪,于我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,是因为它哺育我成长,须臾不可分离;陌生,是因为在拥有它的日子里,几乎从来没有仔仔细细地端详过它的模样。
往田垄深处走去,小麦的清香和着土地的芬芳沁人心脾。极目远眺,一块块麦田密如绒毡,棋盘般整齐,像是心灵手巧的裁缝修剪过一样。微风吹过,麦叶沙沙作响,麦浪起起伏伏,绸缎般绵延向远方。身前身后,一株株青绿色的麦秆,叶片修长挺拔;一粒粒鼓胀饱满的麦粒,密密匝匝,结成小穗。每穗有多少颗麦粒就有多少根麦芒,像战士紧握的钢枪。而此时最容易让人遗忘的是那些不起眼的麦花。和其他植物姹紫嫣红的花不同,麦花极简约、极朴素,它们摒弃了花瓣,没有明艳的色彩,只是袒露着雄蕊和雌蕊,半悬半挂在麦穗上,翘首期盼“风媒”的撮合,将“良缘”化为金黄的丰收。
割小麦是庄稼人一年中的重活,但晒麦子并不比割麦子轻松。记得小时候,打完麦子扬完场,把新麦子运回家,父亲又带着哥哥、姐姐急急忙忙回到地里抢墒犁耙,安插好秋作物,才匆匆返回城里的建筑工地。剩下的重担就全落在母亲身上。
新麦子打下来,要经过连续几天的暴晒才能不生虫不发霉,每年三伏天还要倒缸返晒。以前我家院子地面是土的,庭扫后,等太阳把地面晒得灼烫,母亲就把旧草席、旧被单铺在地上。她踩着凳子趴在缸沿上,一瓢一瓢把麦子挖出来,倒在地上均匀摊开,再光着脚板,双脚交替向前挪动,把麦子犁成麦垄,半个钟头的工夫就重复翻拢一遍。烈日下,一会儿就大汗淋漓,双脚奇痒。后来我家院子铺了水泥地面,再晒麦子就方便多了。那时,每到暑假我都要帮母亲晒麦子。太阳直刺得头皮发烫发木,我不情愿地爬到麦缸里,这边一瓢一瓢地挖,母亲就一簸箕一簸箕地接。缸挖空了,母亲给我擦擦身上的汗,炒个鸡蛋,哄着我吃了后到炕上歇着,她又转身去忙。我一觉醒来,已过晌午,窗外烈日当空,只见母亲正在太阳底下端着簸箕娴熟有节奏地颠簸着麦子,稗子、麦糠、秸秆等随之被筛出,留下的是金灿灿的麦粒。母亲满脸通红,汗如雨下……年复一年,母亲白皙的脸庞上渐渐有红褐色的晒斑皲裂,一头乌黑的秀发变得苍白,硬朗挺直的腰板越来越弯曲了……而今天,院子里只剩下那几口空空的麦子缸还孤寂地蹲在那里,炽热的阳光也只能在香椿树和鸟儿身上跳跃了。
新麦子入仓后,一部分置换成家庭开支以及我们的新衣服、书本费,剩下的就成了口粮,这时满屋子开始飘荡甜丝丝的麦香。母亲心灵手巧,善于调剂生活,她用刚磨出来的麦子面制作面老虎、面燕子、面钱龙、面鱼、面荷叶等,一则庆祝丰收,一则解我们的馋。那时发面不像现在用酵母,而是用自制的“老面引子”。母亲制作的各色面食花样,光滑、白皙、香甜、暄软,奥秘除了揉面有技巧,其他全在“老面引子”的发制、存贮。村子里谁家儿女嫁娶、给老人祝寿、小孩过满月等,总是要找母亲帮忙,她制作的大饽户户传看,赞不绝口。母亲总是说:“不就是抚弄个面团嘛,只要邻居乡亲不嫌弃就行!”这对母亲来说,大概是一种朴素的生活艺术吧!参军以后,我在天南海北的很多城市里吃过很多有特色的面食,面粉更精,造型更美,但怎么吃都找不到记忆里的感觉。
布谷——布谷——在一阵清脆的布谷声中,我缓过神来。哦,望着眼前这片哺育我长大的土地,我恍然想到,这布谷鸟啼落的可是满地跳跃闪烁的碎金子!麦浪滚滚,故土情深。有泥土般厚重的自信,有麦穗一样饱满的情怀,脚踏实地向前走,我们生命的原野会愈发蓬勃粲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