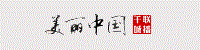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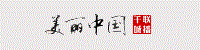

钟志红
一
整整四天过去了,天气不见一丝的好转,作祟的沙尘暴依然如狼群齐嗥,没有分秒的消停。我们只得老老实实地蜗居在土坯房屋里,任凭天地颤动……
这年的春节,在新疆打工的朋友回乡后对我说,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,为了花大力气治理沙漠、珍惜土地,已出巨资进行植树造林,有效改善恶劣的自然环境。开春后,从企业下岗在家待业的我,别无选择地跟随他踏上了戈壁滩。
春寒料峭,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,处处可见堆砌的冰雪;在前往三百公里外的克拉玛依市,沿途鲜见一颗树木、一根青草;接后,又往阿勒泰北行了约两个小时,终于进入准葛尔盆地的西北、到达了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的目的地。
荒芜无际的戈壁,自然无以提供惬意的居住环境,没有电力和手机信号,也没有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无人区,没有电,没有水果、蔬菜,手机也没有信号……
屋内,我见残烛将燃尽,忙再燃上一支,心愿这一盏微弱的星火,能够驱逐肆虐的沙尘,邀来明媚的阳光。桌上,数瓶当地产的“奎屯”白酒已见了底,只有十余张菜堞大小的馕饼,可供我们支撑两天。馕,是新疆的主打食品。我第一次食用时,生硬的馕太有劲道,吃到半饱程度,腮腺早已痛胀,口腔也咯出了血。
负责这片千亩植树工作的只有4个人。他们称我四川——大伙都这样按着个人所属的省份相称,省去了姓名的繁琐。由于今年植树量太大,所以除了山东和贵州外,多招收下我和我的朋友。
一会儿的功夫,一瓶白酒没转上两圈,似乎就见了底。依照老规矩,由打牌输的最多的贵州出门去水箱取水,然后灌在酒瓶里,这样还能转上几圈。可外面的风力实在太大,把房门抵的死死的……
半晌,贵州趔趄而归。不待放下水桶,便兴奋地直嚷:“喂,你们看到了吗,亚娟种的那棵沙棘树竟然没被吹倒呢,像一名女侠客……”

二
若是天气不差,半个月来一趟的生活供会给我们送来面粉、饮用水和蔬菜肉类。车会隔一次载着亚娟来。她是植树单位下派的监管员,也负责给我们发放月薪,最忙时,她每月都要跑几十个植树点。
一个月里,唯一一次见到唯一女人的机会,自然令人期盼。由于路途远,亚娟会吃了中午饭才回去。虽然前后只有一两个钟点,但我相信,她带给我们的喜悦感觉不是薪水完全能够代表的。
说实话,亚娟身材颀长背影很是受看,但面庞不是很漂亮,皮肤黝黑又粗糙的不老少的皱纹。在戈壁上长年的风吹日晒中,女人想美丽并非易事。但女人自有的特质和资源,也是不容置疑的,特别是她站在我面前时,一时也不知道手脚如何搁是好。
亚娟来时,不会到移动房外的土灶前看上一眼的,也没人舍得让她劳作,把她捧作仙女下凡还来不及。再说,她每次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,是去看看屋后她种植的那颗沙棘树苗。
7月的那一次亚娟来,她很不舒服,在4张床中选了我的床躺下。司机说是不是中暑了,要知道这时戈壁滩上的地表温度可达到70、80摄氏度,加上驾驶室里没有空调,男人都受不了不说女人了。
那天,这女人可真幸福了一把,我们都围着她的床前转,仿佛都是罪人般。可是,我们对她的关照是不得要领的,那怕递上一杯水、一张热毛巾。过了一会儿,她就急着证明不是中暑这么回事,是女人每个月一次的“事”来了,她急着找地头“办事”。这是憋不得的事,开车往城里去不现实,但也不至于在太阳底下走到几百米外吧?她急得快哭了的样子,怪可人的。我也不知为什么猛地想起沙棘来,可那树还太瘦小,不具有枝繁叶茂的遮蔽功能。但树坑挖得还算深。
我问她,你相信我吗?她点头。
就这样,我监督大家在屋内,让她在树下解了急。

三
戈壁滩每天不是风沙满怀豪情,就是太阳不嫌劳累。在佳肴美味飘来都见馊味的天地,也只有男人才出现的地方,这里的雨水的确没有男人心里的泪水多。
亚娟那天走后,我心里不知何故地难过,眷恋还是失落,一时也分不清楚,眼前一直有她的影子在游弋。
屋外,偶尔划过一声孤狼的嗥声,皓月当空,多情地从窗口钻了进来。烛光下,贵州再喝得多,也还能摆上一副练功的坐姿;山东拉开了嗓音,开始吼起家乡里不知哪个民族的小调,歌词是他到了新疆后自己杜撰的,我大概记得有一段大意是说,傍晚时分,小伙来到姑娘的窗外装扮孤狼,嗥声里尽是些“想你”,被唬住的姑娘只好去村口幽会……
山东不唱了,他唱不下去了。我发现烛光在他眼眶里有了折射的光泽,如果让我说出口的话,那一定有泪水的作用。
那夜,我梦到了亚娟,像一朵沙棘花……

四
8个月过去了。离开新疆最后一次见到亚娟时,我还在沙地。那几天,我不知道她会在哪一天到来,所以一直都在靠近沙棘的地方挖树沟,想单独与她说话。
她来的时候,离午饭的时间还早,当时戈壁上刮起三四级的风,远远地看着她朝我这儿走来,风撩起她的衣襟和长发,让我的脸煞是潮热。看来,有了上一次的事件,她也许觉得我与其他人相比更值得感激吧!
她招呼我,可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沙棘:“四川,他们都回去了,你还没干完呀!”
我吱唔着,没敢正视她。
她又问:“你来这也该有小半年了吧?嗯。你孩子有多大了?读初中了。男孩女孩?女孩。女孩好呀,不像我们家的儿子,成天陶气陶气死了。”
我笑了笑,埋头抬脚抖了抖鞋里的沙砾,觉得心情轻松多了。
说着说着,亚娟扭着头问:“你媳妇一定很漂亮吧,四川有山有水的,山水育人,你咋不带她一起来呢?”她也觉得这样问多少有些问题,忙说:“也是哈,这戈壁上,就是女人愿意,你也不忍心她三天就成徐娘半老哈!”
亚娟说,她的父亲是陕西人,只是她出生在新疆,再也没有离开过,丈夫是油井的工人,粗人一个,一点也不懂得体贴女人。
“是不是西北男人都这样?”她问。
我不置可否。
这一天,司机一直在修车,亚娟也只好留下吃晚饭。亚娟当然知道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,因为工资都给结算清楚了。山东炒了三盘子的肉菜,是我在新疆吃到最多的一次,亚娟也喝了不少的酒。
借着酒劲,大伙坐在戈壁滩上神侃一通,但当说到分别后的生活,人人不再言语。看得出来,亚娟虽然有些醉意但酒量不低。
亚娟说:“我梦想儿子十年后能考上北京的大学,那样她也有机会去看祖国山河,这些年植树造林、治理风沙的经验和成果,让更多的人国人知道并为之骄傲。”
亚娟还说:“我文化不高,谈不上大的理想,一辈子只想、也只能为植树的事业跑跑龙套,也算为戈壁多一些绿荫、少一些沙砾作出一些贡献……到那时,中国东南西北中都是青山秀水,自己的皮肤肯定也会洁白、细嫩起来的,人自然会更漂亮了。咯咯。”
我接过话:“这是你种下沙棘的初衷?”
亚娟沉默好一阵子,说:“沙棘树苗是父亲生前从老家带来的,他说它在老家可有知名度了,沙棘不仅是当地农产品品牌,更是乡愁的胎记——沙棘对土壤没有讲究,只要有阳光和温暖,就是它的果实,寓意着红红火火、幸福美满……”
我若有所思。
亚娟问我:“你呢?有什么样的梦想?”
一股酒气从心里涌入鼻腔,我被呛得咳嗽不迭。
“快看!”顺着亚娟的手指方向望去,天空中一颗流星闪电般地滑了过去,异常醒目。她痴痴地看了许久,天真的样子猛然把我从惆怅中拽了出来。
她说:“快朝流星许个愿吧,很灵验的——就是一个梦,也能实现!真的!”
我没有如亚娟所愿,但我愿以一首歌送给她,权当分别的礼物:
远方的天空下有一双眼睛,
那是你向流星盼我回归的心,
……
流星飞呀飞过谁未完的梦,
流星飞呀飞过谁许过的愿,
流星飞呀飞过我松开的手,
流星飞呀飞过你握紧的爱……
五
从新疆返家后,我对妻说起亚娟。她说了一句:“她,就是戈壁滩的一株沙棘。”

作者简介:钟志红, 籍贯四川,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。1985年以来,先后在数百家国内外报刊发表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等千余篇,百万余字,获各奖项百余件(次)。